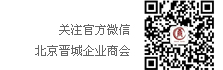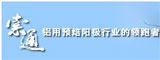晋商先驱王泰来

文化争鸣
——王氏业绩的十二大亮点
王泰来名自振,字宏宇,号泰来,晋城市泽州县秋木窊南沟村人。他由一个草根山民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从挖煤与肩背担挑营运盐输起家,发展为明末与清代的天下大富。因其泰来商号遍及华夏各商埠重镇,史称“泰来贸迁之字号各处有之”。由于声名显赫,民间与社会即将泰来之名作为其各代的共称。
王氏虽具有南城、中堡、北“皇宫”(假紫禁城)的秋木山庄与巨额的金银财宝,但却远离封建社会中“为富不仁”与行商中之弊。五代人恪守“仁义贤孝、诚信公平”的八字家训,竭尽全力为便民谋生计,不惜破家为国佐军需。仁义贤孝之誉闻名遐迩。康熙四十年诰封泰来氏三代人为光禄大夫,赐御书御制“古稀人瑞”匾,康熙六十年又赐“义高北嶽”额。雍正、乾隆时期对王氏更是屡封累赐。王氏五代人故后,民间感其恩、念其德众自聚金为其建祠年以报享,知州佟国珑为其撰《王光禄祠堂碑记》;康、雍、乾三帝的首铺大臣为其各代铭墓。此等殊荣不说绝无仅有,也实属罕见。此虽距今已三四百年,可王泰来仁义贤孝的故事在太行山上仍是盛传不衰。
关于王氏的发展轨迹,我在《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中已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但面对六十多万字的书,让读者有望而却步之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稀人瑞”王泰来,了解明、清时代泽州大地商帮的光辉史诗,故不顾已是耄耋之年,将王氏家族的发展业绩浓缩为十二个亮点,以飨读者。
在明末与清代,泽商是山西商帮中一支活跃而名声显赫的商帮。明代进士沉思孝在《晋录》一书中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说明晋商中的泽商,早在明代已发展起来,而后由南向北推进,最后在晋中一带登上了顶峰。这是所有研究晋商学者的共识。
王氏第一代王国宾,由一草根山民从挖煤与肩背担挑营运盐输起家,在万历时已具有相当规模。第二代王自振以他的奇才大勇从万历经泰昌、天启、崇祯二十多年时间,即将泰来所营盐、茶、票之业,推进至赵、燕全境、大江南北、西域蒙疆。其店伙、人役是几千还是上万谁也说不清楚,时人传下来的说法是:“只知泰来之家日食胡椒一担”、“泰来出行走遍天下不住别人家的店,不吃别人家的饭。”故清顺治立国时,《志》有“秋木窊王氏国初时富甲一郡”之记。第三代王璇高中不仕回庄子继父业,将泰来之业推向了兴盛高峰。据乾隆十七年出版的《永宪禄》载:“王庭扬(王璇次子)泽州人,富甲山右。泰来其贸迁之字号各处有之。查家有现银一千七百万两有奇。”
据《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载:“富可敌国的泽州尹寨河环山堂祁家,始发于清康熙年间。大兴土木在雍、乾时代。祁氏曾挂过据有土地两千亩的牌子。时称,祁家出行从尹寨河到胡北老河口,都有自家的商行、店铺、土地和佃户,一路上人不住别人家的店,牲口不吃别人家的草。且其宅第宏伟壮阔比之祁县的乔家、太谷的曹家、灵石的王家大院一点也不逊色。”与王氏、祁氏先后同时代泽商中的巨贾大富像高平侯庄老南院的赵家,从丝绸起家的高平牛村李家;阳城上伏的赵家、阳城的玻璃世家乔家;沁水西文兴的柳家等等,何则数十家可计。但《志》记“清国初时富甲一郡”者,唯王氏一家。再从发迹时间之早,占有市场地域之广,拥有财富之巨而论,泽商翘楚也非泰来氏莫属。若说宅第,王氏的南城、中堡、北“皇宫”(假紫禁城)的秋木山庄,现尚传世的《鹤栖堂集》有《秋木山庄八咏》。
可能有人会说一提晋商,人们会首先想到海内外闻名的祁县乔家大院乔致庸,何以王泰来能为晋商先驱呢?对此,需从四个方面说明:
一是晋商之称是涵盖山西全境之大小商帮于其中,既非“太、平、祁”所独有,也非“泽、潞”可独占。
二是除上述《晋录》中所记外,明谢肇涮所著《五杂祖·卷四地部》中描写当时资产量雄厚的徽商和晋商时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渔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这不仅说明晋商学者认为“晋商源起于山西之南而后逐步向北推进的共识”的正确,也充分证明了“泽、潞”商帮在明代已是晋商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劲旅。
三是再从晋商内部看:晋商学者张正明先生所著《山西商帮》书中,对晋商名声显赫的巨贾大富,排了十四家。首当其冲的第一家,就是明中叶曾显赫一时的蒲州(永济)张氏。大意是张氏第一代思诚,元末徙蒲州避难,以父传子之序传友直、中亨、克亮、锈、宁、谊、允龄。第八代的允龄年幼即掌家政,力勤攻读。年长遂发奋服贾远游。“拮据20年足迹半天下”,经商半生,但获利不多。直到第九代,允龄长子张四维登科出任京官,其弟遐龄成婚后开始出外经商,凡六七年穷而归。其三子张四教善于经商。利用四维京官势力大发其财,张氏资产不止十倍其初。是蒲州著名富商,系官商结合的大族。(历经至九代而发迹,每代以二十五年计,九代是何概念,发迹何时不言自明)第二家是“官商王氏”(此不细述)。第三家是“首富亢氏”。平阳亢氏,自清初发迹。是商业、典当业和兼营地主的家族,资产有数千万,堪称山西首富。另有一说法是李自成与清军在山海关兵败后退出京师,途经平阳将其所携带的大量金银一部分寄存于亢家,亢氏因此而大富。并据李华先生考证,亢氏是一个持富骄横,悭吝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从上述可见,张、王两家虽先后与泰来氏大体上为同时代的发迹者,但其均为先官后商。唯王泰来是从草根山民肩背担挑起家,历经三代至王璇时已将泰来号之业发展至高峰,且仁行义举誉满华夏成为当时著名的大儒商,故而康熙皇帝诰封王国宾、王自振、王璇为光禄大夫,赐“古稀人瑞”匾。
泰来四、五两代人开始做官后,不但其泰来号业绩未因利用官势而发展,且多系为国为民(后文详述)之付出。至于山西大富亢氏虽纯系经商之家,但清代才开始发迹。而名声显赫的祁县乔致庸乾隆中期发迹,比王泰来迟140多年。据此而论,明代人著述所描述商帮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其富甚于新安”之说,必将自然而然地非泽、潞商帮莫属。王泰来的晋商先驱是历史实践中的产物,若舍此还可其谁呢!
四是王泰来既为晋商先驱之人,那在前些年媒体传播晋商的火红时期,其何以在全国无名、省内也几乎排不上队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才疏学浅,无能评品。只能借三位学者大家的几段原文加以说明。
浙江大学和北师大历史系的杜正贞、赵世瑜两先生早在2006年即在《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一书中指出:“在关于晋商的研究中,泽、潞商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以致晋中票商几成晋商的代名词。实际上,明清泽潞商人以经营盐铁、丝绸等闻名天下,同时在地区性贸易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晋商研究成果迭出……唯对泽潞商人研究略少……仿
佛明代出自泽州、潞州并十分活跃的商人群并不存在有较大影响的活动,对地方和周边社会发挥作用。”学者冯潞先生在《藏富山中的秘密》文中指出:“当然,这不能全怪有关学者和晋中人,他们有他们的理由,让一部分文化元素先亮起来,也是一种可操作方式。这里的问题在学术文化上的跟风,只看见眼前的,而不去从模糊里发现新的。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亮者更亮,黯者更黯。另一个反思是,所在地域及其学者的迟钝和麻木,其行者背后是思想的僵硬。——一个简单的思路——晋商本来就是山西商人的总称,怎么可能就晋中一域呢?”
王氏泰来号营输盐、茶、票的三庄,遍及华夏之各商埠重镇,号称“日进斗金”。清顺治立国时“秋木窊王氏富甲一郡”;《永宪录》在一“议叙山西捐赈人员折”中称:“王庭扬泽州人,富甲山右。泰来其贸迁之字号各处有之。查其家产有现银一千七百万两有奇。”
张正明先生在《山西商帮》一书中,曾对晋商除亢氏(清初发迹)外光绪时资产在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的山西十四家富商列有一表如下:
据上述可见明代人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其富甚于新安”之说与《永宪录》载泰来家有现银一千七百万两有奇而论,说王泰来资产之巨晋商中莫能有出其右者
1
泽商的翘楚,晋商的先驱
2
资产之雄厚,在当时的
晋商中莫能有出其右者
姓 资产额 住 址
侯 七八百万两 介休县
曹 六七百万两 太谷县
乔 四五百万两 祁 县
渠 三四百万两 祁 县
常 百数十万两 榆次县
……(以下从略)
3
王氏第一代王国宾,虽出身贫苦但曾明经。其立的家训是:以“仁义贤孝”为作人的安身立命之基,以“诚信公平”为行商做事之本。他阐述八字的要意是“做人当以仁为重,行事当以义为先;在家孝悌和睦;行商诚信公平;可上当忠于王事,下当体恤黎民”。
其子王自振明经不仕,在商界大展宏图;第三代王璇,顺治十五年中进士却不入仕而回庄子继父业。其弟王珣高中武进士诰封明威将军,但仍不仕归里,辅兄将泰来之业推向巅峰。王氏“仁义贤孝,诚信公平”的八字家训代代谨守,史称“历代长厚”。其为民不惜破家救灾济贫,修太行古道百二十里,办乡学,焚积券,助孤老。万民感其德为王氏建祠以祀,知州佟国珑为其祠写碑记。当朝首辅陈廷敬撰文称:泰来氏“行周礼相周相恤之法,则天下不为灾而民不困于岁。”康熙四十年诰封王国宾、王自振、王璇为光禄大夫,御书御制“古稀人瑞”匾、六十年又赐“义高北嶽”匾。
故时人称:“王泰来是大儒商,是做人的楷模、做事的典范。”
4
◇朱廷礼
救灾济贫不惜破家
王氏济贫不仅“设义学、焚积券、排难解忧”,且逢灾必救,不仅不分地域,并救得彻底。山东灾即输银以济,四川荒即输银以帮。雍正元年(1723年)太原、静乐、岚县、寿阳等十余郡遭大饥荒,泰来即输银八万两。泽州地处太行山绝顶,三年两头不是旱荒就是虫灾或疫病,王氏更是灾必救、贫必济,而且救得扎实,济得彻底。以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年,泽州全境遭虫、旱大灾为例,五郡上百万饥民嗷嗷待食,王氏即以着人联系各地了解灾情、设多点舍粥、饥家给粮、县境外输钱、出银募工捕蝗(虫)等五法赈济。用粮千万担,输钱千万两。弄得家粮用尽,银到外地购粮用完。泰来店号面临停营运之困。在此情况下,多人力劝停赈,泰来却说:“即是破家,也誓欲要救州民得活……”结果,“州民得救而不流离。”时人称:“救活了斗谷人马(一斗米谷其数粒几何?)”当朝首辅陈廷敬对此撰文称:“晋郡县大梫蝗蝝遍郊野,公出钱数十万募人捕瘗,我公分口食食饿者,公亦捐粮周给,州人以故不流离。呜呼,周礼相周相恤之法,行则天下不为灾而民不困于岁。”
王氏五代,代代如此,故“府、县志”中称:“清乾隆二年(1737年),泽州大水,晋普山间洪水暴发,南村、西峪一带平地水深数丈,田舍淹没,人多溺死。”王氏第五代“王镠出银数千万两为众多死者掩埋尸骨,为生者煮粥给食,亲友有逋负代偿至数千金,其他助友恤邻、好义乐施不可殚述。王氏家世积善,五代存其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