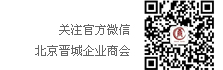赵树理故居—— 永远的草根情结
 |
|
赵树理故居一隅 |
作家赵树理的故乡与我的家乡不过百里之隙,可是我却一直没有去过。起初,我并没有将他视为写作样板,甚至觉得他的作品 “土气”。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写作的磨练,我却越来越敬仰他。敬仰他的文笔,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大旗虎皮,用农家话写农家事,趣味丛生。敬仰他的为 人,情系底层农民,始终如一,从故土出发时是什么样子,到了省城京城还是什么样子。这种文格和人格并驾的高度,绝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抵达。终于有机会,我来 到了地处太行山腹地的赵树理故居,走进了这样一位大作家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
赵树理故居在山西沁水县尉迟村,村边那条清流名为沁 河,1906年9月24日,赵树理出生在沁河边。赵家不是富户,可光景绝不算差,这从遗留的房屋可以看出,虽然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雨剥蚀,农家院落的风骨依 然不减。小院有正房,有厢房。正房坐北朝南,厢房落卧东西两面。这样的院落在北方并不少见,少见的是,正房为二层楼阁,东西厢房也是二层楼阁,阁楼上那一 米高木围栏的镂空雕刻,精细剔透,不无江南亭台楼阁的雅致。
就在沁河边的这个小院,赵树理度过了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这里,祖父和 父亲教他《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等传统经典,还要求他学以致用。用得好不好,天天有记载。先是划道道,做了好事划竖道,做了坏事划横道。后来改变了 方式,备个罐子放豆子,做了好事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幼小的他,就把自己的根脉往仁爱和善良的深处渐渐扎去。在这里,赵树理开始品尝农人的艰辛。每日 天不亮,就被母亲唤起,扒一碗小米饭,喝一碗稀米汤,怀里揣上几个山药蛋,接过父亲套好的毛驴,赶着上路。毛驴在前头颠达,他在后面攀爬,一天下来筋骨都 能拆开。
赵树理就这么在小院中长大。十九岁那年,他考上了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意气风发地走出了小院,告别了田园。
走出了小院,却没有忘记小院;告别了田园,却没有忘记田园。父亲汗滴禾下土的艰辛,母亲纺织到天明的苦累,还有驮炭路上遇见的那些可怜的逃荒者、战战兢 兢敲开院门的讨饭者……都深深嵌进他的血脉。他的内心涌动着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要安得的“广厦”当然不是有形的屋舍,而 是无形的广宇。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这股胸中的波涛恰好对应了革命的浪潮,于是,赵树理再不是一个企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家子弟,脱颖为一个“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的时代新人。
“草根”赵树理出发了,成为一名作家。在那个年代,作家可不像今天遍地丛生,要是用他的生花妙笔养家,非光宗 耀祖不可。可是,赵树理是去闹翻身的,他的笔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解放劳苦大众的武器。他喜欢“解放”这个词语,他要解放劳苦大众,不光是从肢体上解放他 们,还要从精神上解放他们。《小二黑结婚》就这样问世,一经传开就引起热烈反响。小二黑、小芹、二诸葛、三仙姑……一个个小人物,或代表先进思想,或维护 封建意识,矛盾冲突中展示翻身解放的曲折,曲折中却迸溅着光明的火花。赵树理让无数个小人物带着大众的意愿,在他搭建的小说舞台上不断出场,不断演绎。 《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三里湾》……赵树理的作品和他作品中的人物广泛流传,不仅在文化人当中,也成为平民百姓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不倦话题。
当然,也不乏带着挑剔眼光审视赵树理作品的学人,审视的结果是两个字:土气。丁玲看过赵树理编的秧歌戏《娃娃病了怎么办》,写道:“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的干部。”这不是丁玲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不少延安文化人的共识。
或许,赵树理完全可以变个花样,换个新招扮靓自己,他有这样的底气,他阅读过西方的名著,接触过洋人的玩意儿。有次与几个文人闲聊,谈到契诃夫的《在避 暑山庄里》,赵树理不仅能说出故事和情节,连其中的假情书都能背诵出来。写作过赵树理传记的作家陈为人就发现,在赵树理早期的文章中,连意识流也玩得溜溜 转。可是赵树理就是赵树理,他绝不放弃自己的“草根”气息。他投身革命是要解放穷苦贫民,奋笔疾书也不能背弃穷苦贫民。他把深深思考过的道理,化为小说故 事,再用人人听得懂的话语写出来。诚如他自己所说,我写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政治上起作用,人民群众能看得懂。
正缘于此,赵树理的小说拨动了无数农民的心弦。
正缘于此,赵树理开创了“山药蛋”派,并成为领军人物。
遗憾的是,同样是这个赵树理,同样是这个写作路子,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是解放区那片小天地里文学创作的“旗帜”,十多年后,全国解放了,天地更为广阔, 赵树理本应更加放开手脚施展才华,然而非但没有,他还失去了头上曾经拥有的光环。失去也罢,竟然还一次又一次受到批判。面对这种失常的状态,赵树理却仍然 坚持己见,这不由让人想起杨万里的诗句:“却有一峰忽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
赵树理为何不动?说到底,还是草根情结的牵绊。他无法背 叛乡村,背叛乡亲,背叛在尉迟村古老的小院深深埋下的仁爱和善良根脉。1957年担任尉迟村干部的吕学谦说,那时村里人均粮食每年只有二百斤,家家饿肚 子,赵树理回村一看,可急坏啦!他赶紧找关系帮助乡亲们解困,鼓励大伙儿种桑养蚕,增加收入,补贴生活,同时,谋划村里长远的生存出路,并让他们去西沟村 参观学习。
赵树理在阳城县挂职县委副书记时,县委书记曾计划粮食亩产超万斤。赵树理在一旁说,这个不实际吧。书记忍住气接着鼓动,棉花 亩产要达到两千斤。赵树理又插话,这个指标也太高。书记强忍住气,继续讲粮食总产翻十番,赵树理又说办不到。书记忍不住了,一拍桌子说道:照你这么说,是 “大跃进”错了?真是老“右倾”,绊脚石!赵树理也不示弱,回敬道:你这是不管群众死活的瞎胡闹!
个人的命运难免在时代中浮沉。好在终究尘埃落定,乾坤明净,再看赵树理,任谁也不能不对他的文品和人品产生敬意。
如今,当我站在尉迟村赵家小院,往事纷纭,思绪翻飞,却也无法填补这故居的空落。
赵树理从这里走出去了,赵树理的后人也随着他的步履走出去了。小院只能用深长的寂寞收藏往日的生机。不,小院还有生机,是一棵树,一棵冲出屋檐直逼云天 的大树,树干笔直笔直的,树叶葱绿葱绿的。它一定能看见山脚下赵树理的墓园,对正打坐在墓前的作家说:我们的根,都在这里!